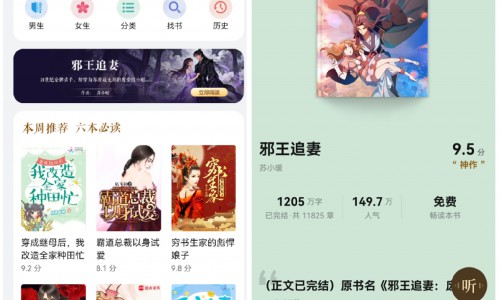你我脑中所映 是否同一月色-原本以为自己是一个个例,慢慢发现,其实身边人大多如此,辗转多处...
陈朝
从联觉现象,到人类经验的研究困境。
现代神经科学的发现不断让设计论者感到难堪。人,万物的灵长,曾被说成是神依据自身形象创造的。然而深入探究我们的大脑就会发现,脑袋里挤下的800多亿神经元没什么像样的顶层设计,反而像是狡黠租客私拉的电线,不断在原有基础上满足新的功能、产生新的适应。每一个人,从最睿智到最愚鲁的,头上都顶着这样一团乱糟糟的器官。这还不算完,《星期三是靛蓝色的蓝》(以下简称《星期三》)想要告诉我们,所有人的大脑都很乱,只不过有些人比其他人要更乱一点。
这是一本关于联觉的书。所谓“联觉”(Synesthesia),又译作“通感”,指的是不同感觉关联在一起。对于没有体验过这种感受的人,包括正在写字的我,都只能通过联觉者的自我报告来体会了。书中收录了许多联觉者的体验:有人会说“字母A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粉红色”,而另一个人则表示不同的数字拥有不同的颜色;有人喜欢吃的食物让他体验到某一类特别的色调,另有人可以从声音中感受到某中形状或触觉体验。
对于没有联觉感受的我们,这种体验太过神奇了。稀缺性与“感质”(Qualia)的独特性,让联觉成了一个古怪的难题。稀缺是指大多数人没有感知过它,甚至没有和联觉者面对面过。而“感质”的大难题在于,你没法体验别人体验到的感受。你可能从来没有体验过联觉,也可能是一个尚不自知的联觉者(什么?原来其他人听音乐时看不到那些彩条?)。《星期三》一书至少能从现象上回答一些问题。
人群中到底有多少人是联觉者?早在现代心理学的童年,人们就发现了联觉现象。1880年,著名的生理和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收集各种各样的人类数据,从他观察的人群中发现了能看到“带色彩的数字”的人。根据他的观察,每20个人里就有一个联觉者。但是1993年的一项调查却认为,每2000到2500个人中才有一个联觉者。此前大部分测试都基于自我报告。2005年,有学者设计了客观的测试,结果发现,每23个人里就有一人具有某种联觉,能看到带颜色的字母或者数字的人大约为1/90。这个数字恐怕比我们设想的多了不少。由于研究也无定论,关于上面这个问题姑且放一放,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问题:联觉的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古怪,可能没有两个人的联觉体验完全一样,甚至也许要一一列举才能记录各种可能性。常见的联觉体验包括感受到数字和字母的颜色,给日期赋予颜色,对不同的音高和音色感受到色彩或触觉体验,等等。我们只是大致知道哪一种体验真的常见。可即便是较为常见的数字与字母的颜色,联觉者所感知到的也因人而异。书中的一个例子是,那个认为字母A是粉红色的女孩的父亲也是一个联觉者,他们曾经争论过数字5的颜色。两位来自专业领域的本书作者列举了大量鲜活但个性化的联觉体验,这些体验有一些共性,但是对于每一个个体,这些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于是我们很难真正沟通这件事:蜘蛛侠没法向你解释什么是蜘蛛感知,超人也说不清他是怎么透视的。
那么问题来了,联觉是一种天赋吗?看起来似乎是。不少联觉者是艺术家,著名作家纳博科夫就是一位联觉者,其写作中也涉及了自己独特的体验。如果真是如此,联觉者就比非联觉者在艺术领域多了眼睛和耳朵和嘴巴和鼻子和身体……那么自然有这种可能性,一些艺术家中的联觉者还将自己的感受体现在了创作之中。作者注意到,许多联觉者是艺术家,不过他们同时也清楚地知道,这个数据来自自我报告。就我们迄今所知的层面而言,可以说联觉体验能提供艺术灵感,因为它给事物提供了更多的感官线索,也有利于记忆——一些联觉者可以用自己的感受记住本来无甚规律的信息。在此之外,说联觉提供了什么更多的生存优势,就没什么数据支撑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联觉呢?答案是我们还没弄懂。现代神经科学已经对人类的感觉通路有了相当的了解。我们知道从光线进入视网膜到形成视觉信息,信号如何在大脑中传递和处理,我们知道声波如何牵拉了耳蜗中的毛细胞,产生的电信号又是在哪里转化成了听觉。联觉,毫无疑问,来自于不同感觉通道的交互作用。过去十几年,联觉从报纸上的奇谈版块进入了神经科学的实验室,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猜测它的由来。第一种可能是,我们的大脑发育要经历一个神经联结减少的过程,青春期时童年形成的联结会消失一部分,大脑随之进入成熟过程。这个消失的过程叫作“剪枝”,每一个普通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而联觉者可能保留了更多剪枝前的通路。另一种理论则认为,大脑的兴奋与抑制构成平衡,跨感官的联系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被抑制了,而联觉者却抑制不足。但不论是哪一种假说,都没有形成定论。已经能够考察基因、脑电和功能性核磁共振下活动的人类大脑的我们,仍然没能解决联觉的神经机制。
好了,看到这里,我反而对能否用現有方法发现联觉的秘密十分怀疑。可能有人还在怀疑:联觉真的存在吗?如果不存在,这个世界上就有成千上万未经串通就众口一词的骗子,为了吸引一点可怜的注意力而编造自己的特殊感受,这种感受虽然千差万别,但也有相当的共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联觉问题也确实涉及了联觉乃至心理学、神经科学的根本问题:如何研究个体。教科书告诉我们,科学心理学在19世纪末诞生于欧洲。在那个时代,内省和自我报告还是被科学界接受的方法,然而随着行为主义等方法的兴起,人们意识到自我报告并不一定靠谱,想要“科学”的心理学,就应该使用可操作的定义、观察外显的行为,就应该用统计的方法发现差异与相关。因为这种方法的转型,关于联觉的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几乎被遗忘了,直到90年代对于大脑的研究有了新的工具和方法,联觉研究的论文数量又陡然提升。
然而工具与方法的革新并非全部。即便是过去20年“新潮”突起的功能性核磁共振研究,大部分的实验依旧针对的是群体,探求的是平均数。如果我们承认联觉者体验的个性化来自于非常个性化的特点,那么如今的神经科学至少无法发现所有联觉的秘密。《星期三》一书提供了足够的现象而非机制。但是这种现象足以引发思考。从古代的佛教思想到现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型,几乎所有关注人类认知的哲学思考都在关注一个问题:人类的经验是共通的吗?我们的体验是一致的吗?如果我们感知的世界如此不同,我们又如何交流呢?看起来,同一个月亮还是映照在一切水上,但是联觉提示我们,还有精妙而微小的差异分布在人群之中,你我脑中所映的并非一模一样的月。这月相殊异的机制,等待着科学技术和方法的范式转换。
美国作家、神经科学家戴维·伊戈曼(上)与理查德·西托维奇合著的《星期三是靛蓝色的蓝》